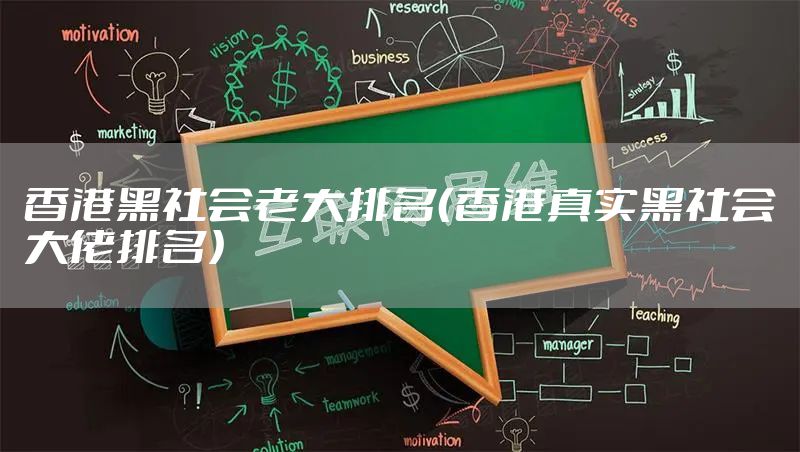含聿诗句,自古便是文人墨客笔下的雅致意象。聿者,笔也;含聿者,执笔沉吟之态。在《礼记·曲礼》中便有"史载笔,士载言"的记载,这里的"笔"正是聿的化身。唐代杜甫在《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》中写道"握聿持策何从容",将文人执笔时的气度描绘得淋漓尽致。宋代苏轼更在《与米元章书》中直言"得公诗,把聿三叹",道出了对佳作的珍视之情。
纵观中国诗歌长河,含聿意象最早可追溯至《诗经》时代。虽然《诗经》中未直接出现"聿"字,但"彤管有炜"(《邶风·静女》)中的"彤管"实为早期笔具的雅称。至汉代,扬雄在《法言·问道》中明确提出"孰有书不由笔",将笔提升到文明载体的高度。魏晋时期,陆机《文赋》开篇即言"余每观才士之所作,窃有以得其用心",操觚含聿"的创作状态已成为文人的自觉追求。
唐代是含聿意象的鼎盛期。李白在《草书歌行》中挥毫"墨池飞出北溟鱼,笔锋杀尽中山兔",将执笔的豪情与天地万象相融。杜甫更在《饮中八仙歌》中描绘张旭"挥毫落纸如云烟",展现了中国书法与诗歌的完美结合。白居易则以其平易诗风,在《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》中记述"笔砚为辘轳,吟咏作縻绠",把文人日常的书写状态化作诗意的劳作。

宋代文人将含聿意象推向新的境界。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虽未直言执笔,但"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"的感悟,正是文人放下聿笔后的哲思。黄庭坚论书法则云"心能转腕,手能转笔",道出了执笔与心性的内在关联。陆游晚年作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中"此身合是诗人未?细雨骑驴入剑门"的著名诗句,看似与笔无关,实则暗含了诗人随时准备执笔记录的诗心。
明清时期,含聿意象更趋细腻。文徵明在《题画》诗中写道"闲窗弄笔临摹处,绿叶黄花香满衣",将执笔作画与自然景致巧妙融合。清代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强调"诗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",道出了执笔创作的本质在于真性情的流露。纳兰性德《浣溪沙》中"被酒莫惊春睡重,赌书消得泼茶香"的佳句,虽未直接写笔,却将文人雅集中执笔唱和的场景描绘得如在目前。
含聿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。首先它是才学的具象化,《晋书·张华传》载"陆机兄弟见华一面,即曰'此君龙跃云津,顾彦先凤鸣朝阳,皆南金也'",龙跃云津"正是对文思如泉涌的生动比喻。其次它代表着文人的责任担当,范仲淹"先天下之忧而忧"的千古名句,正是秉笔直书的典范。再者它象征着艺术的至高境界,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中"虽无丝竹管弦之盛,一觞一咏,亦足以畅叙幽情"的书写状态,成为后世文人追慕的典范。
在传统书画艺术中,含聿更发展出独特的审美体系。唐代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提出"意存笔先,画尽意在",强调执笔前的艺术构思。宋代郭熙《林泉高致》中"笔法记"专论用笔之道,指出"一种使笔,不可反为笔使"的创作真谛。元代赵孟頫提出"书画同源"说,其《枯木竹石图》题跋中"石如飞白木如籀,写竹还应八法通"的见解,将执笔技法提升到哲学高度。
含聿意象还深刻影响着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。文房四宝的讲究,书斋陈设的雅致,无不围绕着执笔创作展开。明代屠隆《考槃余事》详细记载了笔格、笔床、笔屏等文房清供,反映出古人对执笔环境的极致追求。清代《闲情偶寄》中更将"文人之事"细分为"执笔、展卷、焚香、烹茶"等十三个环节,构建起完整的文人生活美学。
当代社会中,虽然毛笔已不再是主要书写工具,但含聿意象依然焕发着新的生命力。在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中,书法教育重新走进课堂,国学讲座座无虚席,文人画创作方兴未艾。这些现象表明,含聿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仍在延续。当我们品读"含聿诗句"时,不仅是在欣赏文字之美,更是在与千年文脉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从《诗经》的比兴到汉赋的铺陈,从唐诗的格律到宋词的婉约,从元曲的通俗到明清小说的世情



 相关阅读
相关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