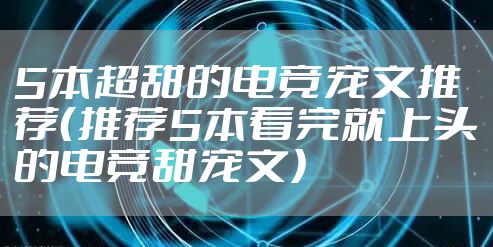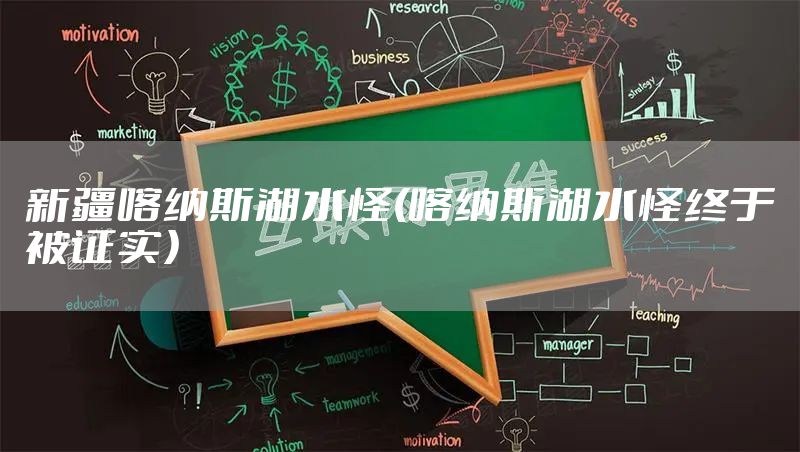"云母屏风烛影深,长河渐落晓星沉。嫦娥应悔偷灵药,碧海青天夜夜心。"李商隐这首《嫦娥》道尽了月宫仙子的孤寂与永恒。在中国诗词的长河中,赞美嫦娥的诗句犹如银河繁星,闪烁着中华民族对月亮最浪漫的想象。从《淮南子》"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,姮娥窃以奔月"的古老传说,到李白"白兔捣药秋复春,嫦娥孤栖与谁邻"的深情叩问,这些诗句不仅描绘了月宫仙子的绰约风姿,更寄托了文人墨客对永恒、孤独与超越的深刻思考。
唐代诗人笔下的嫦娥形象尤为动人。李商隐在《霜月》中写道:"青女素娥俱耐冷,月中霜里斗婵娟",将嫦娥与霜神青女并置,突显其不畏清寒的高洁品格。皮日休《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》"玉颗珊珊下月轮,殿前拾得露华新。至今不会天中事,应是嫦娥掷与人",更是将月宫仙子想象成慷慨赠予人间桂花的天上仙灵。这些诗句既展现了嫦娥的仙姿玉质,又赋予其丰富的人性温度。

宋代词人对嫦娥的赞美更添哲理韵味。苏轼《水调歌头》"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"虽未直呼嫦娥之名,却将月宫仙子的传说融入对宇宙人生的追问。晏殊《中秋月》"未必素娥无怅恨,玉蟾清冷桂花孤",则通过嫦娥的孤寂反衬人间的团圆之可贵。这些词作在赞美嫦娥的同时,也完成了从神话传说到人生哲理的升华。
元明清时期,嫦娥形象在戏曲小说中愈发丰满。白朴《梧桐雨》中"嫦娥离月殿,仙子下瀛洲"的唱词,将嫦娥与杨贵妃的形象相互映照。李汝珍《镜花缘》描写月宫"琼楼玉宇,晶宫贝阙",更是极尽想象之能事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吟咏嫦娥的组诗,如明末王彦泓《寒词》十六首中,多次以嫦娥喻指坚贞不屈的品格。
当代诗词创作中,嫦娥形象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。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发射时,众多诗人以"嫦娥"为题创作新诗,传统意象与现代科技完美交融。这些作品既延续了古人对月宫的向往,又展现了中华民族太空的豪情,使千年传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纵观中国诗词长河,赞美嫦娥的诗句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打动人心,在于其完美融合了三种美学特质:神话的奇幻之美、诗歌的韵律之美和哲理的深邃之美。这些诗句不仅是语言艺术的结晶,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、生命、永恒等终极命题的诗意回答。当我们吟诵"嫦娥应悔偷灵药"时,既是在欣赏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,也是在体验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共鸣。
从《诗经》"月出皎兮"的朦胧咏叹,到现代航天科技的具象呈现,嫦娥形象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。这些赞美嫦娥的诗句,如同夜空中永恒的明月,照亮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,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。在每一个月圆之夜,当我们仰望苍穹,这些美丽的诗句便会自然涌上心头,让我们与千年前的诗人共享同一片月光,同一种感动。



 相关阅读
相关阅读